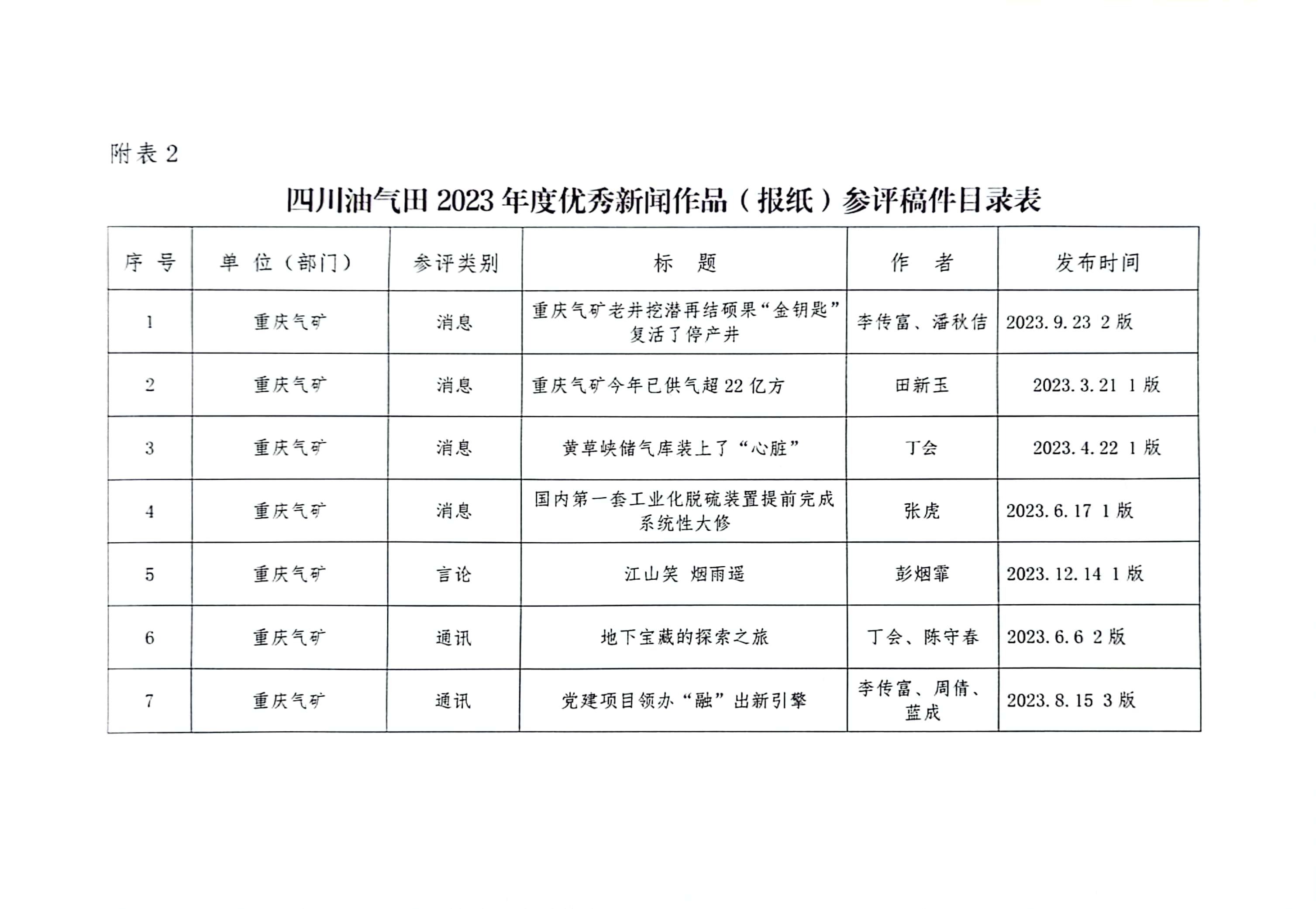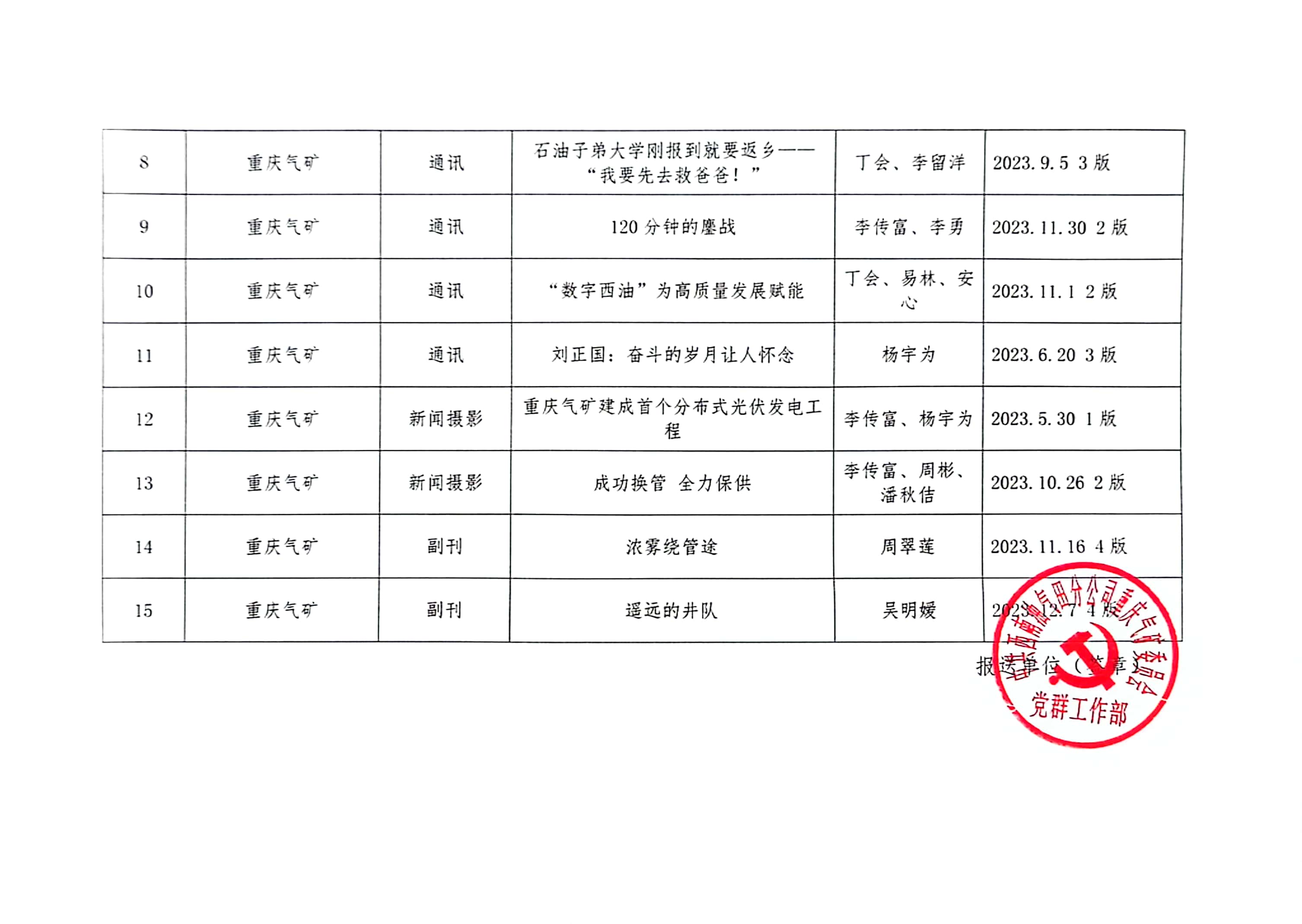遥远的井队
吴明嫒
我小时候跟随母亲生活在米仓山南麓的一座村落里,四面环山。小小的我,时常站立在院坝的中央,仰头看着高而深远的天空发呆。
大山之外,有县城。县城之外,有父亲。
母亲不识字,家里最初的书信往来由叔叔代劳。每次收到父亲的来信,叔叔都会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件,卖关子似的在我们眼前晃动着。母亲笑而不语,我们三姐妹甚是着急:“叔叔,拆开念啊!”叔叔这才取出信笺,凑到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读起来。我们瞪大眼睛,紧紧盯住叔叔一张一合的嘴唇,屏息聆听。
父亲的信里,除了日常问好,会告诉我们他目前在某个地方打井,汇点钱款让家里应急。末了,一定是那句“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不知道父亲在哪儿工作。母亲一会说在石油沟,一会说在卧龙河,后来她也说不清楚父亲所在的钻井队到底去了哪里。据说好几年春节,父亲都是在搬家的敞篷车里度过的。
从父亲的零星来信中,我知道父亲工作的地方有高耸入云的钻塔,有轰鸣的机器声,有夜晚如白昼一样的星星点灯。
有一年寒冬,二伯和叔叔去过一次父亲的单位,他们回来后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在钻井队的所见所闻。
叔伯们来到钻井队,父亲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谓之为“开洋荤”。二伯和叔叔闻言满心欢喜,各自端上洗脸盆欣然跟随。说是澡堂,其实就是一座锈迹斑斑的铁皮房子,父亲大手遥遥一指:“我马上要去钻台处理急事,你们自己去吧,好好洗个澡,解个乏。”
二伯和叔叔好奇地走了进去,只见里面有一排竖起的管子,管子中间有阀门。他们俩各自站立在一根水管下,一人试探着去转动阀门,居然头顶上的管子口出水了。这一发现令他们兴奋不已,另一人模仿着打开阀门,一根细长的水柱冒了出来,两人欢快地冲到水管下,打算酣畅淋漓地洗个澡。不一会,一人喊冷,一人喊烫,两人交换着来回奔跑,总算洗了个囫囵澡。
在钻井队期间,父亲给他们吃了一种水果,细长的,黄色的,像弯弯的月亮一样的,剥了皮来吃,香甜可口。
听罢,我的好奇心上来了,水管子的水怎么会一冷一热呢?长得跟弯月一样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呢?
一个像笑话,一个像童话。
二伯和叔叔讲得眉飞色舞,可谁也没有给我想要的答案。
村子里用水要到很远的一口古井去挑水,大冬天洗澡挺奢侈。我们一般会在大年三十用做豆腐碾压出来的浆水洗一次澡,第二天着新衣迎新年。所以,二伯和叔叔觉得此次钻井队之行终生难忘,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我跟父亲也去过一次钻井队。天刚麻麻亮,父亲将睡梦中的我顶在他的头上,行走在山间密林的小道上,脚步声急促,虫鸣蛙叫声不绝于耳。至于怎么到的县城,又怎么辗转到的钻井队,我浑然不知。记忆中的父亲总是一身油乎乎的工装,脚蹬一双大头皮靴。
在钻井队,我挨过一顿严厉的批评。一次和父亲在食堂吃饭,我见一块肥肉上有几根猪毛,便嫌弃地扔到了地上。父亲顿时火起,一拍桌子,大声地呵斥我:“捡起来,吃掉!”父亲对我一向皆是慈爱有加的,从来没有打骂过我。我惶恐无助,一下子大哭起来,不明就里地捡起地下沾着灰尘的猪肉,含着眼泪吞咽进肚。
随着我们的成长,读父亲的来信和回信,最先是姐姐,后来是我,我跟遥远的父亲有了直接的心灵沟通。
有一天,我们跟着父亲进了“石油城”,解开了盘旋在我脑海里的许多问号。原来洗澡有冷、热水两根水管,通过阀门调节,混合成一股水流,调节到适宜的温度,就可以洗上美美的热水澡。
香甜可口如弯月一般的水果,原来是香蕉呵。
经历过饥馑之年,靠几个红薯活下来的父亲,深深懂得粮食的珍贵无比。那顿骂,我不冤。
人生的很多困惑直至豁然开朗,回首已是万水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