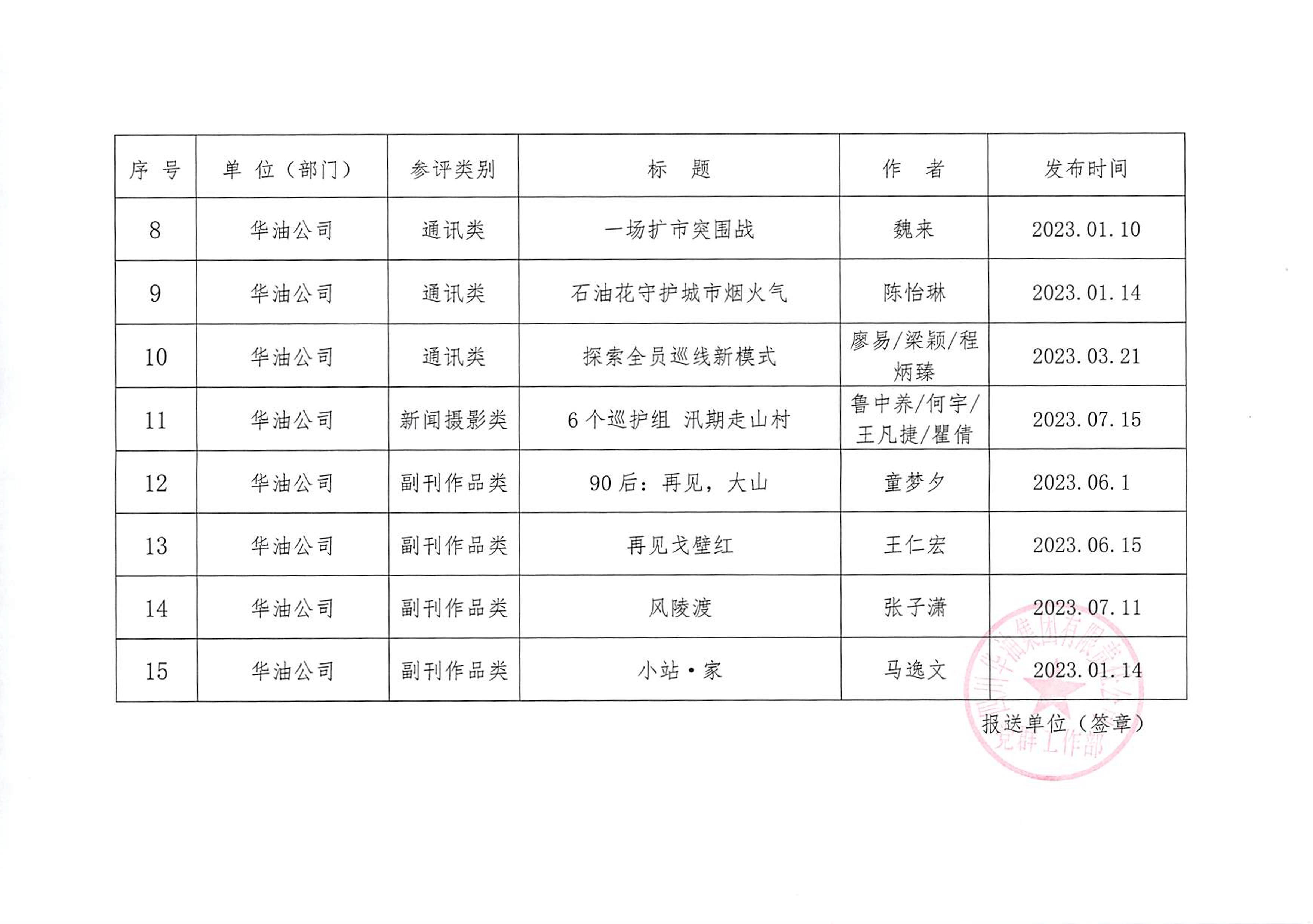90后:再见,大山
小时候的我,对大山充满着好奇。
每到月初,母亲就坐上长得像黄色大拖鞋的皮卡车去往大山里,待到月底才回家。回家两天,月初又走。周而复始。我好奇极了,大山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直到上了小学,寒暑假的时候,我也坐上了黄色“大拖鞋”,从城市去往不同的大山。我不知道那些山的名字,只能用母亲上班的输气井站名称来区分,亭一井的山、石板配气站的山、七里二十五井的山、黄龙四井的山……
新鲜劲儿一过,方方正正的输气站场里就没什么好玩的了。母亲反复告诫我不能靠近黄色和红色的管子及设备,规矩太多,我便往站场外跑去,在大山里避暑过冬。
夏天,正是山里的开花时节。在母亲上班的值班室里偷拿几个纸杯,一人一个分给小伙伴们,结伴往山上走。寻着粉紫色的身影去摘绣球花、循着沁人的香气去找黄桷兰,来点格桑花点缀,再抓一把路边不知名的红果,心满意足地端着一杯“插花”回家,放在母亲宿舍的玻璃桌上。在小伙伴的呼唤中又匆匆换上拖鞋,往山下去了。对着山口矗立的牌子稚声稚气地读着“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顺着山路走到山谷,光脚踩踩溪流里的鹅卵石,再打个水仗,这一天才算完美。
等花谢了,天冷了,大山里自有另一种玩法。
井站门口那家农户是姜婆婆一家。姜婆婆一头短发,黝黑瘦高,看起来就干练勤劳。我常常窝在她家的柴火灶前,看姜婆婆往灶洞里送几把柴,用火钳在滚烫的灶灰里刨个坑,埋几个红薯,然后端个小木凳放在灶前让我坐下,嘱咐我乖乖守着红薯,她便转身忙碌去了。
村里的厨房总是黑黢黢的,只在屋顶侧边留个天窗。一束天光照亮屋顶上挂着的香肠腊肉,也被屋内热气烘出腊味的气息。我盯着灶洞里火焰的跃动,冬日寂静,木材燃烧的爆裂声格外清脆响亮,却成了我的催眠曲,时针分针似乎都打起了盹,听不见光阴流逝的脚步了。
直到姜婆婆拨开灶灰,红薯香味飘来,我才悠悠转醒。吃着姜婆婆帮我剥好的香甜红薯,再拿一个回家给母亲尝尝。走出黑黢黢的厨房,我才发现自己的涤纶运动裤上被火星子烫了个小洞,好在母亲并没有责怪我,只是让我下次离灶火坐远一点。可冬天寒冷、屋内黑暗,我总忍不住想往灶火前凑近点,盯着火焰跃动,一切都慢了下来。
大山的面貌在我的脑海里只有夏冬两色,春秋季的我被皮卡车拉回城市里,做个老实的读书郎。过了几年,汽车拉着我去了别的城市,绿皮火车又带我到了更远的地方,母亲也不再进山。
后来,我见过鲜花盛开在小小的花盆里,鹅卵石铺在鱼缸底,明亮的白炽灯不够温暖,腊味也不再充盈满屋,我渐渐熟悉那些黄色和红色的管子及设备,却再也没有到过大山里的井站。
从大山到城市,时针分针似乎跟我一样,走快了些,童年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变小的拖鞋、变短的运动裤、变不见的大山,都是它在跟我挥手,说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