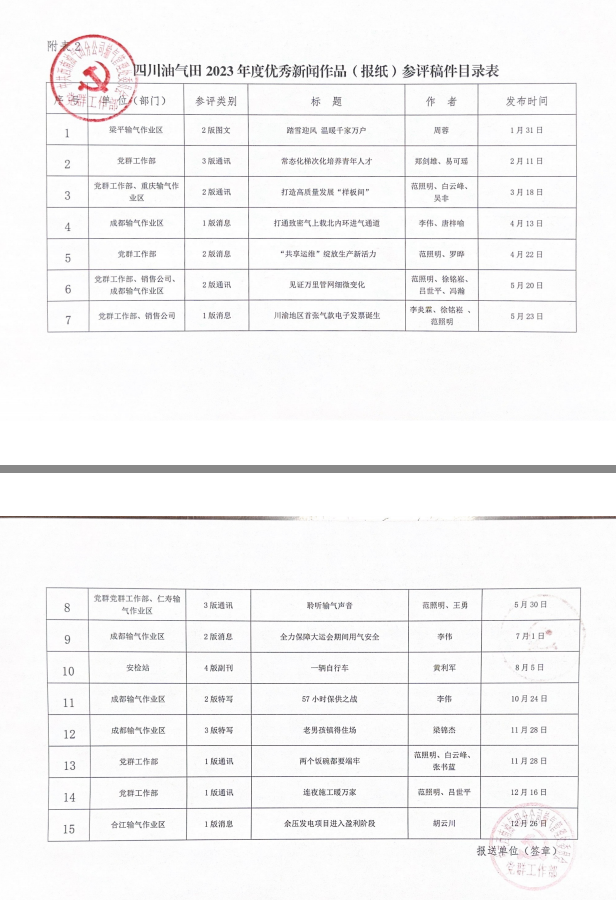一辆自行车
趁着周末好天气,一家人到郊外玩了个尽兴。返程时,发现单元楼墙角斜躺着一辆自行车,车体早已锈迹斑驳。看见它,突然想起了父亲曾经拥有的那辆自行车。
那是一辆“二八”圈永久牌载重自行车,听母亲说,那辆车比我还年长一岁。
母亲是石油工人,单位离家很远,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还没有交通车,生活条件很是艰苦。怀上我那年,有一次母亲背着10斤猪油走了好几里路,回到家里,已是筋疲力尽。父亲心疼母亲,一跺脚,买了这辆自行车。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隔三差五就逃学去摸鱼、用弹弓打鸟、逮蜻蜓,每日乐此不疲。一次逃学回家,父亲看我满身污泥,一气之下,一脚踹来,我躲闪不及,从墙的这头倒在墙的那头。至今我都很感谢那一脚,大概父亲被我倒下的姿势给吓着了,从此再没踢过我。我记得很清楚,父亲那天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鞋,以至于成年后,我对黑色的皮鞋始终存有阴影。
虽然父亲脾气暴躁,对这辆自行车却极其爱护。他叫母亲给自行车的横杠和座垫各打了一个皮实的“外套”,后架也做了一个更结实的支撑。一有空,父亲就把脚蹬、车架、车把、挡泥板擦得锃亮。凡有轴承的地方,隔段时间就会打上适量的润滑油,轮胎随时都保持充气饱满。时间长了,还把车倒过来,用工具紧紧链条、校准方向、调整车的舒适度等。被父亲精心呵护的自行车,骑上去像风一样顺畅,一按铃铛,声音清脆响亮。
自从有了这辆自行车,母亲怀我那一年,下班后就再没走过路。记得小时候,一家人出远门,母亲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我坐在横梁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家里的大米几乎都靠它驮运回来。有一年春晚,郭达推着自行车在台上演小品《卖大米》,母亲笑着对父亲说:“瞧,像不像咱家那辆自行车?”
中学时,我一直比较瘦小,看见有的同学骑自行车上学,心里很是羡慕,于是软磨硬泡着父亲,希望他能教我学骑自行车。因为我个头矮小,即使把座垫放到最低处,双脚依然够不着踏板,只能用一只脚从横梁下插到另一端的踏板上。父亲很担心我的安全,先用手扶住车的后架,然后一直小心翼翼地跟着我在车后跑,一圈下来,满头大汗。
有一年,我右腿的膝盖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脓疮,严重到没法走路。到医院去,医生说要动手术,母亲坚决反对。她不知从哪里听说外敷能够治疗,于是找到一家中医院,每日换药的任务就自然落在父亲的头上。那段时间,我每天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父亲拉着我穿过大街小巷,这大概是我懂事后与父亲最长时间的亲密接触。我们一路聊学习、聊生活,甚至聊到了怎么玩。我突然发现,平日一向严肃、言语不多的父亲,也有随和的一面。
多年前的一天,自行车停在楼道时丢失了,父亲不善言辞,非常懊恼没有保管好自行车,一个人憋着气难受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成家后,因为在异地,每个周末都会给母亲打个电话问候一声。看见墙角的自行车,我突然体会到那辆失去的自行车承载了父亲对家庭太多的关爱,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主动联系过父亲,主动问候过父亲,心里便隐隐生出一些愧疚。
回到家里,我赶紧拨通了父亲的手机,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很平淡,不过这一次我们爷俩却聊了很久很久……
放下电话,我想,或许世间的父爱就像一杯芬芳醇厚的清茶,沁人心脾,回味悠长。
(黄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