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书国:通往《自然》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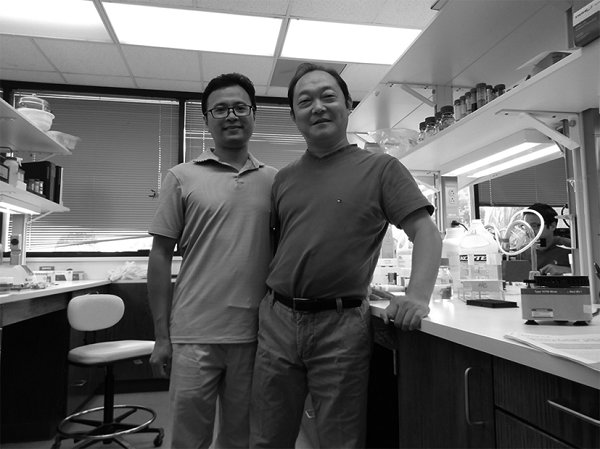
2021年 9月,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侯书国副教授首次在《自然》子刊《自然-通讯》发表了研究成果,这是山东建筑大学首次以第一完成单位在这个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2022年 5月 4日,他终于以共同第一兼通讯作者的身份登上了《自然》正刊,这也是学校历史上又一个“首次”。
这个研究成果,是关于一类结构全新的植物细胞因子 SCREWs和 NUT,它们相当于植物体内的
“哨兵”和“监工”,当病菌侵入或者外界环境变化的时候,它首先会发现并传导信号,调动免疫系统来保护植物机体,增强植物对病菌或者恶劣环境的抗性。这个创新性的发现,对于促进生态良性循环和粮食安全问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众所周知,科研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脑力劳动,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每一个成功者背后,都有荆棘丛生。从 2007年入职山东建筑大学,侯书国已经在植物-环境互作领域默默耕耘十五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汗水浇灌,终于结出硕果。回首这十五年的经历,他庆幸自己坚持到底没有放弃,也衷心感谢学校、学院给予的全力支持和宽松工作环境。
板凳甘做十年冷
侯书国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学霸,相反的,他说自己“起点非常低”。他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7年 10月入职山东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当时学院刚刚成立生物工程专业,急需专业人才,他成为了一名实验教学中心的管理人员。那时他还从未发表过学术论文,但他早就对自己有了长远的规划,他喜欢搞科研,选择了基础研究这条道路,就一门心思走下去,无论多么寂寞坎坷。
正因为觉得起点低,侯书国一刻都不敢放松,每天都在努力“爬坡”,学习学科前沿知识,电脑里已存下了几千篇顶级期刊的文章。2012年,在符合在职读博条件的第一年,侯书国第一时间申请到山东大学读博,为了心中的科研梦想继续深造。仅用了三年时间,侯书国在兼顾学校工作的同时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还被评为当年山东大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读博士期间,一篇发表在《自然》期刊上关于动物先天性免疫的论文,和他在山大所做的研究碰撞出灵感的火花:也许,植物体内也有类似动物的保护机制?基于这个超前的想法,2014年侯书国以实验师身份申请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并获批,从此踏上了通向《自然》的漫长路程。
开始阶段,项目的进展举步维艰。因为基础研究偏重理论,侯书国在校内难以组建并肩作战的团队,也缺少实验所需的硬件设施,他把目光投向了国内外其它高校,先后联系过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同行专家,寻求合作。
2015年博士毕业,侯书国立刻申请前往美国德州农工大学访学,在那里他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并认识了对他的研究至关重要的两位合作导师:何平教授、单立波教授。2017年底,侯书国的研究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定要想办法创造团队,哪怕是只能在线联系的‘跨国研究团队’”。在何平教授等“跨国研究团队”帮助下,侯书国的想法一步步得到验证,一个全新的植物细胞因子慢慢揭开了神秘面纱。
收获的季节如约而至。2019年,侯书国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在《细胞》子刊《植物科学前沿》(TrendsinPlantScience)在线发表了热点评论文章,2021年在《自然》子刊《自然-通讯》发表了研究成果,2022年登上《自然》正刊。
在这个一直向上“爬坡”的过程中,侯书国认为自己从来没改变。从没有改变的是他相对单纯的性格、相当单调的生活,还有最重要的,是对科研的热爱。
非宁静无以致远
因为对科研的热爱,侯书国痛并快乐着,基本每天都泡在实验室,白天待一整天,吃过晚饭又遛弯回到实验室,即使是假期和周末,只要家里没事他也会到实验室继续工作。他并不觉得日复一日的重复实验很枯燥,反而认为聚餐喝酒没什么乐趣。他不热衷人际交往,但并不排斥必要的社会工作,从不缺席需要他参加的会议。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耐得住寂寞才能在基础研究的路上走到最后。对大多数高校“青椒”来说,从事基础研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选项。需要长期的苦干也很难有成果,又不能像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一样拿到横向课题,只能申请最纯粹的纵向课题,资金不足甚至连版面费都付不起。在多数人看来,既然搞基础研究只能拿到工资,那还不如给学生上课,至少压力小,还能多拿课时费。“我发 NC的版面费,就是合作单位主动帮我付的。”侯书国回忆说。
侯书国非常理解那些为了适应学校要求和个人的发展而放弃了基础研究的高校“青椒”,但他自己却固执地坚持了十五年。“我是因为有兴趣有热爱,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他觉得自己的性格适合搞科研,从事别的工作会事倍功半。长期的科学研究,也让他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方式,转换到另一个不同的赛道意味着舍弃以前的一些积淀。他也想过转换赛道,只是研究领域偏重理论,与建大其它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难以融合,不舍得放弃,就只能坚持下去。
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的党政领导班子,也完全理解基础研究的困境,和侯书国一起坚持着,无论是他读博、访学还是创造实验条件,学院都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基础研究很可能做一辈子也没什么成果,学校应该给科研工作者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能急功近利,要慢慢积累。”“侯老师就是个很适合搞科研的人,他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王洪波说。
相对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成果产出通常只能依赖论文的发表,在《自然》《科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全世界基础研究工作者的终极追求。很幸运,侯书国做到了。“我也有遗憾,我的起点太低,尽管一直马不停蹄往前走,但今年我已经 42岁了,如果能在 40岁之前拿出成果,那么就会有更多机会,国家对青年教师倾斜的政策也会有机会争取,这对学校和我个人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春种一粒“粟”
除了在实验室培育植物,侯书国的另一种快乐来自于在教学中培育学生。尽管实验室的工作足以满足学校要求的工作量,但侯书国还是主动承担了两门面向大一学生的课程《普通生物学》和《生物工程导论》。
在生活中不善聊天,在课堂上却能滔滔不绝,把他了解的学科前沿信息传递给学生。下课后,常常会有学生两眼放光地找到他:“老师,我对做实验很感兴趣,能不能跟着您做实验?”每当此时,侯书国就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这种独属于教师的幸福感让他逐渐爱上了教学。尽管不断有学生加入实验室,也不断有学生跟不上节奏而退出,但最终会有学生留下来,而离开的学生也会因为这段经历而认清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所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多考虑个人的发展,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意识到身上的责任感。如果我的言传身教能给这些孩子启蒙,在他们心里种下科研的种子,也许以后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发芽开花结果,这是当老师的意义,也是我的幸福感的来源。”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播下“种子”总会有所收获。侯书国对一个叫康寿凯的学生记忆深刻,这个学生虽然资质一般,但身上有一股不放弃不服输的劲头,从他身上侯书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简单的实验屡次失败,侯书国告诉他不用再做了,实验不成功是因为实验设备不稳定。但他还是不服气,自己又做了五六遍,终于基本过关。后来,康寿凯考到山东理工大学读研究生。若干年后有一天,侯书国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从美国华盛顿一个著名实验室打来,是康寿凯在那里攻读博士后。侯书国又一次感到了强烈的幸福感,用自己的影响力把学生引导到适合的人生道路,帮他们培养科研的兴趣和信心,是他实现了身为教师的人生意义。至今,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彼此分享对方在科研上的成功与失败。
“我希望年轻人能坚持自己的想法,少受外来干扰,要及早认清自己能干什么,如果是干科研的料儿,就坚持下去。”
对侯书国来说,纷至沓来的赞誉都是属于过去的成绩,他时刻在提醒自己要继续保持不骄不躁的心理。而未来需要奋斗才能创造。科研是他的初心和使命,他一步一个脚印,仍然坚定地走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