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珞珈山,做一场敦煌梦——————“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纪略奔赴万里:从敦煌到珞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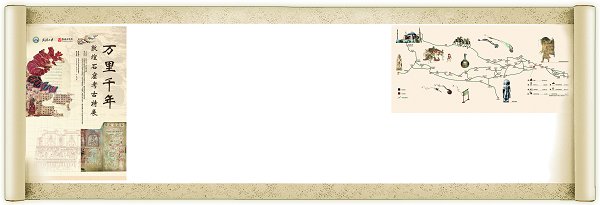







“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相当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
五月的珞珈山,迎来了这样一场文化盛宴:武汉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浓缩于万林艺术博物馆。
踏入博物馆的大门,须臾之间,参观者便可跨过万水千山、穿越历代千年,与敦煌石窟面对面接触。佛像、壁画、龙砖、佛经、刺绣、华盖……这些从敦煌远道而来的文物叙述着古丝绸之路的旧日荣光,展演着中华文明的熠熠光彩。
撰文:施玥馨
摄影:金鑫
5月6日晚,两辆满载货物的甘肃牌照重型卡车驶入武汉大学校园,学校时有车辆出入,因此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几日后,透过万林艺术博物馆的玻璃门,可窥见一尊巨大的佛像卧于一楼中庭,陆续有人驻足围观;5月18日,“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正式开幕。原来,卡车所载的正是从敦煌莫高窟远道而来的珍贵文物。跨越万水千山、拨散历史尘烟,敦煌终于听到了珞珈的呼唤。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精神,让广大师生观众近距离了解敦煌石窟考古学术成果、感受敦煌文化魅力,武汉大学和敦煌研究院共同举办本次“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
展览持续四个月,包括“丝路漫行”“灿烂佛宫”“百年回顾”“重读历史”“历程”“校院联手”“霓裳美仪”“壁上丹青”等几个部分。展厅内,壁画、佛经、彩塑临摹品、复制洞窟等168件/套展品熠熠生辉,展示出敦煌考古的丰硕成果。
展品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亲自挑选,其中珍贵文物30余件,不乏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出国家重点文物和极具学术价值的丝绸之路多民族、多宗教繁荣见证物。绝大多数展品为首次离开敦煌,外出首站即奔赴珞珈山。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表示,本次展览最特别之处在于“这是第一次以敦煌考古成果为主体布展,所以有很多展品是第一次拿出来展览”。
开展当晚,万林艺术博物馆举办“博物馆之夜:梦回敦煌—敦煌石窟考古主题展演”,作为“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配套活动。武大师生以精品歌舞、乐器演奏、服饰表演、朗诵等艺术形式,演绎出流光溢彩的敦煌胜境。15家媒体线上直播,吸引超30万人观看,线上线下的观众均沉醉于敦煌魅力之中。精妙纷呈的表演虽停留在当夜,但属于珞珈的敦煌故事,才刚刚开始。一眼千年:敦煌石窟的前世今生!!!!敦煌石窟是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地,其中的莫高窟于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最早一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之一。它不仅记录了一千多年间建筑、雕塑和壁画艺术的流传及演变,承载着中国中古时期的重要文化;亦见证着古代丝绸之路的沧桑岁月与悠久历史,反映出古代中国多元文化与欧亚文化的长期汇集与交融。
敦煌石窟最早起源于前秦时期。1600多年前,一位僧人在岩壁上开凿了首个石窟。此后千年,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与佛教的兴盛,敦煌石窟逐渐拓展至700多座,大大小小的洞窟内布满精美绝伦的彩塑与壁画,汇集了不同文明、不同朝代、不同宗教的文化艺术结晶。
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则要追溯到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藏经洞中出土了5万余件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从此,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形成了一门国际性学科———敦煌学,也正是由于藏经洞的发现,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和发现了敦煌石窟。
藏经洞的发现引来了一些西方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劫掠,他们在考察中开始以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进行编号、测绘、照相及文字记录。此后国人亦开始对敦煌石窟进行学术性考察与记录。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开始有计划地对敦煌石窟进行重新编号、内容调查、题记整理、图像拍摄等工作,为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敦煌石窟的保护,制定了“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方针,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项研究工作逐步开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敦煌石窟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洞窟断代分期、壁画内容考证等方面均取得重要学术研究成果。
百年间产生的丰硕考古成果与学术成就,离不开几代敦煌学者的艰苦付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莫高人”。敦煌是历史的奇迹,也是“莫高人”用心守护的奇迹。他们秉持“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众心一念、共燃心灯,在漠漠黄沙中甘守清贫,只为守护莫高窟这座文化宝藏。是他们的奉献与坚持,才有莫高窟今日的盛世重光。
或许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敦煌石窟就成为所有莫高人的信仰,这也正是他们愿意坚守的缘由:“不怕风起沙扬,不惧遍地荆棘,秉烛前行在文明的宝库里,除了敦煌已成精神信仰外,心里无他。”“敦煌成了我生命的全部。”“与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为伴,为保护莫高窟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是极大的幸福。”“我是在衰老,而伟大的敦煌艺术却青春永在,魅力长存,将会一代又一代激励后来的献身者,他们会在你伟大的怀抱里继续发掘我们民族无穷的智慧。”为了“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他们默默无声地工作,或许籍籍无闻,但敦煌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自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有一百多对夫妻坚守大漠戈壁,其中就包括彭金章与樊锦诗这对伉俪。
大学毕业后,彭金章来到武汉大学工作,并着力创建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樊锦诗则身赴大漠、扎根敦煌。千里守望近20年后,彭金章追随爱人前往敦煌。在敦煌工作期间,彭金章主持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揭开了莫高窟北区的“神秘面纱”;樊锦诗更是将一生心血都倾注于敦煌,开创我国石窟科学保护方法体系、推动实现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创设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等,极大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两人在珞珈山相爱、在莫高窟相守,为中国考古事业奉献一生。这样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正是千万莫高人的人生缩影。
梦回敦煌:置身展陈之中
余秋雨说,“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在“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中,这种感受尤为深刻。
所有的文物展品并非缺乏灵魂的死物,而是人类生活与历史文明的真实见证。岁月的痕迹横亘其上,文物不言,却能作为桥梁联通古今,让今人与古人对话。
款步进入万林艺术博物馆大门,一尊身长15.80米的巨大卧佛毫无防备地撞入视野。这是莫高窟南段第158窟的复原场景,为莫高窟著名的涅槃窟之一。其左右侧壁分别绘十大弟子举哀图、各国王子举哀图,佛祖释迦牟尼安详侧卧,表现“寂灭为乐”的涅槃境界。这座敦煌卧佛是利用“数字敦煌”和3D打印技术结合的复制品,其虽被分为多块搬运再进行拼接,却能呈现出严丝合缝的展示效果。
除此之外,展览二层亦有三个全景复原洞窟,呈现出意蕴悠长的故事和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价值。其中,第285窟汇聚中西方不同神灵、融合多种绘画风格,被誉为“中国的万神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它亦是敦煌基于整体测绘数据复原的第一个完整的数字洞窟:先使用数码相机拍摄数字照片,再通过纹理映射完成完整的数字洞窟重建,最终获得洞窟的三维纹理模型完成复原。
第275窟建造于公元4世纪,为敦煌最早开凿的三个洞窟之一,内部佛像与壁画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面积最小的第17窟即鼎鼎大名的“藏经洞”,考古学者在其砌墙封闭的窟口背后,发现了大量的佛经、佛画、法器及其他宗教、社会文书等。
复原洞窟的表现形式能够最大限度为参观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信息管理学院学生姚胜译在参观时表示:“走进第285窟的一瞬间,我就被深深震撼到了。仿佛有一瞬间我真的到了敦煌莫高窟,这种全方位环绕的感觉是其他展览所没有的。”
沿台阶拾级而上,敦煌丝绸纹样与各类人物画像在两侧出现,恍若乘时光机穿梭于千年丝路。到达二层展厅,琳琅满目的展品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各类壁画栩栩如生地讲述经典佛教故事,反映宗教发展与文化交融;供养人像等画作中的世俗人物展示古人衣着妆容,得以窥见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嬗变的脉络;多种语言和宗教的经文书写敦煌的丝路传奇,展现出多国家、多民族的文化符号;缤纷颜料在敦煌画工与塑匠手中幻化成缤纷色彩,孕育出具有华夏气派的审美意趣与艺术精神……
还有诸多不容错过的国家一级文物:北朝时期敦煌写经中的精品“大般涅槃经卷”;北朝珍贵实物资料、古代人物肖像珍品“刺绣说法图”;首尾完整的唐代佛经写本“藏文大乘无量寿经”;为数不多的早期写本、研究晋代书法的宝贵资料“东晋《三国志·步骘传》写本残卷”;详细记录酒台总账的“北宋归义军衙府酒破历”;栩栩如生的“五代龙砖”、活字印刷传播见证“回鹘文木活字”等等。
作为本次展览的重要亮点,“重读历史”展区系统展示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成果,这也是神秘的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次走出敦煌。我们通常所说的莫高窟指莫高窟南区,而莫高窟北区则相对神秘。在敦煌工作期间,彭金章先生担任莫高窟北区考古工作的领队和负责人,主持莫高窟北区考古工作。他带领团队经过历时近10年的6次考古发掘,探明了北区石窟原貌、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既有西夏文、回鹘文、藏文、回鹘蒙文、八思巴文、梵文、叙利亚文、婆罗迷字体书写的梵语文献等多民族多语言的文献,亦包括回鹘文木活字、首次在敦煌发现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银币等丰富的文化遗存。北区考古成果的发表为敦煌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此外,展厅内亦全面回顾百年间敦煌石窟的考古工作与成果;回望敦煌石窟背后历代莫高人守一不移、白首初心的坚守与奉献;展现校院合作采取数字化保护,以“数字敦煌”项目为依托,让千年石窟“活起来”的文化遗产发展新局面。
未来之径:校院联手赋予文化遗产新活力
如此重磅的展览之所以能入驻珞珈山,要追溯到武汉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的深厚渊源。
早在20世纪50年代,武汉大学就开始了敦煌文化的研究,逐步发展成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重镇。21世纪以来,校院双方开展全方位合作,相继完成了国家973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石窟三维重建、敦煌智慧数据资源建设与服务应用等重大项目,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2017年,武汉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2020年,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在武汉大学挂牌成立,樊锦诗受聘为名誉院长。当年9月,武汉大学相关方面前往敦煌研究院拜访樊锦诗,共同促成了此次敦煌石窟考古特展。
面对文化遗产损毁的危机,应用现代科技实现可持续性保护与活化利用,是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未来之径。“数字敦煌”项目正是校院合作助力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应用数字技术为文化遗产注入活力的典范。该项目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对敦煌石窟和相关文物进行全面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和存储,将图像、视频、三维等多种数据和文献数据汇集起来,构建一个多元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的石窟文物数字化资源库,通过互联网面向全球共享。
目前“数字敦煌”项目已取得丰硕成果,不仅造就了科学、完整、系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而且广泛运用到了考古测绘、美术临摹、文物保护、展览展示、文化弘扬等各个领域。
2006年,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朱宜萱教授、格林教授与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讨论“数字敦煌”研究方案,自此开启武汉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保护研究合作之路。此后,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多次赴敦煌开展数字化技术试验,在莫高窟地区开展机载激光扫描、地面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精密控制测量等系列测绘工作,实现测绘数据采集,取得系列成果。如成功重建出莫高窟的几何模型与贴图模型;通过纹理映射完成完整的数字洞窟重建,获得洞窟的三维纹理模型;开展崖体变形监测,对崖体形变进行预警等。朱宜萱教授亲赴敦煌考察的影像,已被列入本次展览的展陈之中。
近年来,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主任王晓光教授团队亦与敦煌研究院开展合作,围绕敦煌智慧数据资源建设与服务应用进行探索,为文化遗产数字资产管理与共享服务提供了示范。目前已实现搭建敦煌壁画主题词表关联数据服务平台、研发“五台山图”数字叙事系统与《九色鹿》VR叙事系统等。
校院合作保护文化遗产,是对共同使命的追寻。正如校长窦贤康在本次展览开幕式上所言:“武汉大学与敦煌研究院有着共同的历史使命,那就是深入挖掘阐释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利用现代科技保护和管理,赋予文化遗产新的活力。”珞珈与敦煌的故事不止于此,仍有待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新篇章。
在“万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中,既能通过珍贵精美的文物感受到敦煌文化的魅力,亦可深刻体会敦煌百年考古工作的艰辛不易。这场独属于珞珈的敦煌之梦,将持续4个月。就让我们一同跨越万里千年,聆听丝路梵音,静观佛法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