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风景旧曾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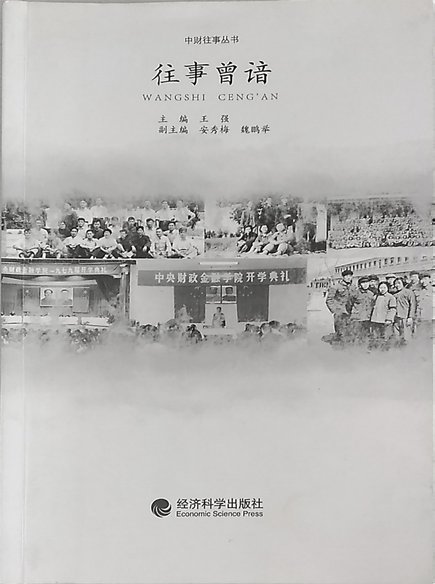





孟子说过,“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见《孟子· 梁惠王下》)。历史是人物构成的,没有人物,就没有故事,自然也谈不上历史。 所以中国人写历史, 就以 “ 纪传体”为正宗,都是人物的故事。
我 1982 年春大学毕业来中央财经大学(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至今已30 余年,可是我认识这个学校已近 50年了,可以上溯到 20世纪 60年代中“ 文化大革命” 初始时。家母是这所学校金融系的教师,我那时因“ 停课闹革命”无学可上,也无处可去,便日日随家母到财院上班, 便也略知这里的一些老师,那都是我的长辈,虽然有些被打倒,但也终是长辈。家母尝为道其事,我自常生敬仰之心,虽然也觉得与当时形势颇显扞格,但总不能将他们作敌人看待,因为当时我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我也并不能把他当敌人。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因革命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者,可我却一时跟不上那革命的脚步,这可能颇受家母的影响。
我真正开始认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以下简称财院),应该是在北师大上学的时候,那时财院刚刚恢复,家母也从北京财贸学校回归到财院。我们北师大离财院很近,财院的大礼堂当时经常放电影,我就骑着自行车来看,闲暇时也常来财院蹭点吃喝。因家母的关系,也就常能看到财院的老师们,也就常能和他们聊天,也就因之渐渐认识了这所大学,知道了些这所大学的历史,脑子里就有了些这里的人物和故事。碰巧我大学毕业又被分配到了这里教书,小时候的那些长辈们一时就成了我的同事,跟他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触。现在我已年过半百,那些我曾很尊敬的长辈们也大多做了古人,可是每每想起他们,便有不尽的故国遥思。
在这里可令我追忆者多多,若删繁就简,我还是想先说说几位名师,比如崔敬伯、崔淑香、凌大挺、张玉文、刘光第。 我不能言其全, 也只是些丛残小语,零星杂记而已。
崔敬伯
崔先生在国初是政府的高级税官,此前在国民政府时也是高级税官。这是我认识崔先生之后知道的,也是尽人皆知的。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曾随家母去看望崔先生,先生貌清癯,其声尚壮朗,耳稍聩,步履略显蹒跚。他听说我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便和我谈诗, 先生旧体诗作得好,有《镜泊诗稿》,音律不苟,意境高远。我那时初生牛犊,与先生纵横捭阖,坐语移日,竟无视先生为财政税务专家,只把他当做文史宿儒。先生那日谈兴甚浓,与我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我从先生那里知道了很多在课堂上不知道的东西,我真没想到在财院还有这样文史功底深厚的老师。从先生家出来已是日落时分,家母说她来这里那么多年也没听老先生说过这么多话,我只跟家母说崔先生太了不起了。家母说,崔先生了不起的还没跟你说呢,他是财税专家。我说财税我不懂,只是这文史功底就足令人叹服不已了!
崔书香
  小时候我管崔先生叫崔阿姨,因为她和家母过从颇深,常来家中做客。那也似是“ 文化大革命” 中,我那时就知道崔先生的老伴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陈振汉先生,“ 反右斗争” 时也是著名的“ 右派” 。崔先生是著名的统计学家,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读过书。20世纪 70年代,财院解散后,崔先生经常来家里和家母聚谈。那时家里没电话,联络不便,崔先生骑着一辆小红自行车从颐和园那边到百万庄我家来,逢家母不在,她就留一张小条贴在门上, 常常是用英语写的,她知道家母不懂英文,但是她说她的汉字写得不好看,又知道我家一个邻居阿姨精通英文,她说可以让这位邻家阿姨作翻译。家母经常拿着崔先生的英文小条激励我学好英语,虽然到现在我的英文也不好,可是那时确实努力地学过一阵英语,动力就是崔先生的那些英文留言。记得我考大学时,从顺义的知青队回家取东西, 正好那天崔先生到家里来,家母就让先生帮我看看英文,先生说,你的英文写得很漂亮,就是错字病句太多。 我当时很不好意思,先生就鼓励我多写多看,而且叫我特别注意多读,要有语感。1977 年考大学,我的数学和英语考得都不错,数学好是因为有财院的程玉英教授让她老伴给我辅导的;英语考得好,就要归功于崔先生那一席教诲了。我到财院教书后很少见到崔先生,记得有一次在校园中见到她,我还和她说起她给家母留英文小条的事,她朗朗笑着说,这事你还记得?我知道你母亲有翻译,我就写着玩啦。她还说我在校报上看到你的书法作品,你的汉字写得真好,我要能写这么好就不留英文小条了。我说您是谦虚,您的英文小条让我一直惭愧没有学好英文。她说中文其实比英文难学。我想这是先生在鼓励我罢了。
  张先生是会计专家,学问亦关乎金融。我小时候叫她张妈妈,不知为什么这样叫。她和家母都在金融系执教, “ 文革” 前就经常到我家做客,我对她印象很深。她常是穿一袭旗袍,坐在那里很端庄,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字正腔圆,一丝不苟。偶尔见她吸一支烟,那姿态也十分优雅。她的字写得好,家父常对我说,你张妈妈的字里有英气,不太像女同志写的。先生亦擅女红,还曾给我和舍妹做过衣衫。家母和我说,张妈妈是在辅仁大学家政系读过的,大学时代也是校花,当时尚可与王光美(后来刘少奇的夫人)争胜。这一点我后来在启功先生那里得到过证实,启先生当时是辅仁大学的老师。我毕业分配到财院后,曾去看望老师,启先生就问我,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张玉文?说她大学时是出了名的美人。而且启先生知道张妈妈的丈夫是梁保罗。梁叔叔我见过,印象中也是很英俊的。可惜“ 文革” 初被迫害致死。
“ 文革” 时财院解散,张先生去了厦门大学,常与家母书信往来,那时到信箱里取信,一看那刚劲的字迹,便知道是张妈妈有信来。张先生好像也是1978 年财院复校时返京的。家父是那年秋病殁,记得张先生来家吊唁,与家母抱头痛哭,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她和家母说:“ 现在终于咱们敢哭了。”因为当时“ 文革” 已经结束,虽然家父的政治结论还没做,但形势好了,不那么“ 左” 了,所以敢哭了。想想极左时期,家里有政治问题的人就是死了,连被哭的权利都没有。有的人家甚至强打精神,与死人划清界线,人性被政治泯灭,在那个非常时代已经司空见惯了。
1982 年年初我分配到财院后,经常见到张先生,我还叫她“ 张妈妈” ,她叫我“ 小同事” 。有一次在老教学楼(已拆除,即现在专家宾馆后面女生宿舍那个地方)听到张先生上课,声音洪亮,一板一眼的,那音质十分吸引人。她讲的是经济课程,我站在门外一直听到下课。她出来见到我说“ 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我在门外听了一节课,她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偷听啊!我说您讲课的声音有魅力。我还问她,“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这在会计学里很重要么?她说很基本,“ 你想学会计?” 我说不。她问“ 那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不是学中文系的么?” 我说只是觉得这话有意思,似乎蕴含着一种平衡的道理。她说,我看你这个小同事挺有意思,中文也好,经济也好,往深里研究都是魅力无穷的。
最后一次见张先生是在主教楼的电梯口,她提着一只菜篮子, 里面有些许菜,我问她,您还自己买菜啊?她说都得吃饭啊,吃饭就得买菜做饭啊,还能锻炼身体。你母亲过世太早,一个是她性格内向,一个是她不会锻炼。时家母已过世有年矣。
凌大挺
  我来财院的时候,凌先生在研究所工作, 家母当时也在研究所工作过一段,与先生交好。我当时正在选注《中国古代公文》,知道财院除了崔敬伯先生,凌先生的古文献功底亦好,就让家母作伐拜见凌先生。先生鹤发红颜,貌若神仙,一口京腔,绵软可亲。那时我知道先生写了茶税史,他还为我讲了许多古代的典章制度。他和我说,若注解古代文书, 要知道古代列朝制度。 他说 “ 三通”是要看的。先生所谓“ 三通” 者,就是《通典》 《通志》和《文献通考》。所以,我在注解时,多去图书馆查阅“ 三通” ,那时“ 三通” 我还没有家藏。
先生旧学功底深厚,亦善丹青,我曾想让先生作画,先生笑而不允,只是说你让你老师启元白画啊,他是名家,我不足论,只是糊口小技而已。我以为只是先生谦逊,也就不坚请。后来我听我的亲戚说过,“ 文革” 时先生遭难,经济上入不敷出,他给人家干过零活,还给绢花厂画过纸灯笼,画一个几分钱,就靠各处这些微薄收入维持家用。如是,我才知道先生为什么说他的画画是“ 糊口小技” 。
先生平时在校园中散步,也是财院一道风景。他常是西式装扮,手执细杖一枝,西装革履,天暖时穿衬衫、吊带西裤,风度翩翩。常和他一起散步的是外语教研室的张建业教授,二老一治专门史,一精于英文,而凌先生专治国史却着西装;张先生精通英文却穿国服,这也是一种“ 中西合璧” ,相得益彰。我在北师大读书时,在校园中就经常看到那些大师级的老先生曳杖徐行,那些老先生身上凝聚着这个学校的文化、传统、学问、文章。一个学校要是没有这些老先生,就如同一个家里“ 家徒四壁”一样。我每见到凌先生、张先生他们在校园中漫步,就觉得我们学校虽小犹好,精神上的堂庑顿觉高大,就像宅院里有老树,厅堂上有名人字画,虽不见得有钟鸣鼎食,但总觉得是诗礼传家。孟子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近人清华梅贻琦校长因之而说, “ 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吾于凌先生等老先生之于中财大,亦如是说。
刘光第
  我之知道刘光第先生,是因为家母和先生在《金融研究》杂志上一起发表过文章,又因为先生与“ 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同名,所以就记住他了。家母和我说,刘先生了不得,他是财院唯一一个读过西南联大的,这更令我心生敬仰。改革初,先生在经济学界多有倡论,我毕业来财院时,就知道他是经济学界的知名教授了。那时家母随财院一个代表团到南方考察,带队的是姜明远院长,还有张玉文、刘光第等耆宿。他们归来后,我在校园中见到刘先生,自报家门,说了家母的名字。先生说,我听说你来财院供职,好啊,你们一家两代人都为咱们学校作贡献。只是你若学经济就更好,咱们国家现在缺经济人才啊。从那时认识了刘先生就经常在校园中见到他。见到他也就是鞠一鞠躬,叫一声刘先生。先生也就欠欠身,笑一笑就过去了。只是有一次跟我说,你还是叫“ 先生” ,现在好像不习惯这么叫了。我说我们在师大念书时见到老先生都是叫先生。刘先生说新社会移风易俗,都不那么叫了,师大还是“ 古风犹存” 啊。我说我还比较习惯这么叫,先生说这样听着亲切,也有师者尊严。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多有政治风波,先生与我们一些年轻人一样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后来我们都被批评,一日遇到先生,先生对我说,我们都是爱国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90 年代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传达后,先生同我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伟大,小平同志就是英明。
1995 年年末我去韩国教书,1996 年先生突然驾鹤西去。我是从同事给我的信中得此噩耗的。当时我在釜山一个禅院中请韩僧为之超度,那感觉不亚于苏东坡在杭州孤山的惠勤禅室痛悼欧阳修的仙逝。
以上所记诸位教授,都是中财的名师耆宿,今虽都已做了古人,但其事迹精神都历历载于中财大史册。一个学校在其历史的一个时间段落有这样一代人,就为这个地方增添了厚重的内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夫子曾云:“ 君子疾夫没世而名不称焉。” 这些老师,以他们的学问文章、人格力量彪炳于中财大,名显于天下,这是我们的财富。一个学校的财富,不在于校园有多大,楼宇有多高,系科有多完备,专业有多丰富? ? 而在于教师之热爱教育,尊重学问,奖掖生徒,境界高远。这就是所谓有大师更胜于有大楼,有好教师更胜于有好设施。好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滋养学生,是能给学生自由之思想,使之有独立之精神。那这老师首先是要有境界的,而且是天地的境界;同时是有学问的,而且是有思想的;还要有悲天悯人之心,对学生能博之以文约之以礼,对职业心存敬畏无私无碍。中财是有过这样的老师的,我们现在仍有这样的老师在无私地奉献着。一个学校因为有了这样的老师,才使学校有光芒、有影响,才会使我们的学生在他的学习阶段不忍蹉跎。(原文刊载于中财往事丛书《往事曾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