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足履实地 行稳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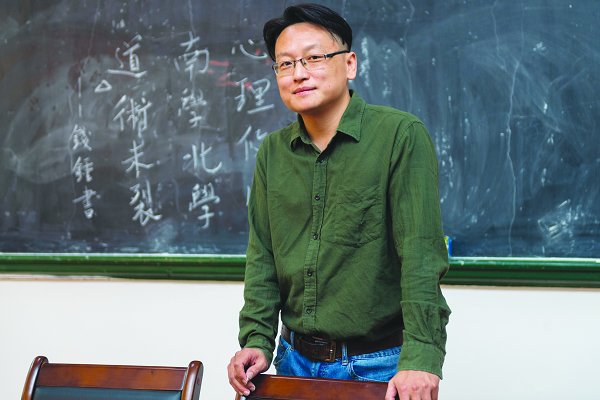
尽管2001年大学毕业后就离开华师,但文学院副教授刘涛觉得,十几年间,他与母校并未“疏远”。在2015年之前的十多年里,他每年都会回武汉待上十天半个月。期间,必会回到华师,看望老师和同学。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他都会听听老师们的想法和建议。2015年,当他以“师资博士后”的身份重返桂子山,刘涛坦言,机遇之外,亦有情感,桂子山是一个能给他归属感的地方。
科研:发现“问题”潜心“打磨”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维视野中的钱锺书文学语言论》和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钱锺书与中国现代学术》;在权威期刊《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字源谬见,诗史之辨与一桩学术公案———论钱锺书对闻一多<歌与诗>的批评》,写文章《论钱锺书的神韵观》与曹顺庆先生商榷……这些年,刘涛一直在从事钱锺书学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大概从2009年起,他开始系统地反复研读《谈艺录》和《管锥编》。他说,这两部著作都不太容易读,确实需要一点耐心,不过读进去以后很有意思。“钱锺书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语言也调皮,有锋芒。”
钱锺书的学术著作是否真如一些当代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是“散钱失串”?他的学术研究是否真的缺乏“问题意识”?他到底有哪些学术创见?对于这几个学术界很有争议的宏观问题,刘涛总想一探究竟。
他深知要弄清楚这些“大问题”,须得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入手才行。空口说白话,口号喊得再响,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如何从钱氏特有的旁征博引中“抽丝剥茧”,析出值得探讨的“具体问题”,这是对耐心和学力的考验。
时至今日,刘涛依然感念陈炎老师的指导和教诲。“准备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开题报告洋洋洒洒写了好多页,语言似乎很漂亮,章节好像也很工整。陈老师看了之后,就问了我一句话‘你要解决什么问题?’。这句话把我问懵了,支支吾吾半天没回答上来。是啊,博士论文十几二十万字,如果都没想清楚要解决什么问题,又没有自己的观点,总是海德格尔这么说,哈贝马斯那么说,到底有什么意义?陈老师强调,关键是你怎么说!”刘涛回忆道,这件事加深了他对“问题意识”的理解,也成为他对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所谓的研究不过是把别人的观点和论证又变相重复一遍。”
“完成一篇好的学术论文,不仅要有‘问题意识’,还得用搜集到的材料把观点论述清楚,逻辑很重要。逻辑思辨能力跟不上,掌握再多的材料也写不出‘穿透力’的文章。”刘涛告诉记者:“陈老师总是提醒我写论文要注意逻辑。当时觉得很有道理,却没有切身感受。做学术研究久了,走了一些弯路,积累了一堆教训,才体悟到陈炎老师的良苦用心。现在看来,能不能写好的文学论文,关键是看数学好不好。这其实是说,除了文学的专业知识之外,逻辑思辨能力特别重要。”
刘涛说自己现在刚刚走出‘学徒阶段’,才摸着一点做学问的门道,尚且不能算是‘熟练工’。一篇《字源谬见,诗史之辨与一桩学术公案———论钱锺书对闻一多<歌与诗>的批评》的论文,从发现问题、查阅资料再到撰写成文,一万多字的论文,他足足写作和“打磨”了近两年。“打磨”的过程无疑是辛苦的,即便有时会“力有不逮”,刘涛依然耐着性子,固守着自己的标准。“我喜欢经过反复推敲和琢磨,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想清楚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刘涛心中,这就是治学的乐趣所在。
埋首于钱锺书学术著作研究多年,刘涛也意识到只研究钱锺书,视野毕竟太狭窄了,今后有必要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钱锺书的著作其实涉及到近现代学术史上的许多著名学者和很多重要问题。例如,在《谈艺录》中,钱锺书点名评论过黄遵宪、王国维、章太炎、严复、苏曼殊等晚清民国的学者名人,也暗中与闻一多、郭绍虞、方孝岳、朱东润等学者有过论争。从问题层面来看,钱氏曾讨论过、唐宋诗之争、文言白话之争、文学进化论、史诗问题、诗史互证、诗史说、等问题。总而言之,《管锥编》虽然写于1970年代,但其中仍可以看到钱氏对20世纪学术热点问题的回应,只不过没有指名道姓或没有直接点出问题罢了。我想今后能以钱著中的问题为中心,以小见大,逐渐过度到对近现代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
教学:“上课”是个良心活
刘涛坦言他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能够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知识,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诚恳地说:“把书教好是教师的分内工作,否则既对不住学生,也对不住良心。”
大约是师承缘故,再加上多年研究心得,在给学生们上“文学理论”这门课时,刘涛不断调整教学方案,希望把概念和理论讲得条理清晰,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尽管已经有十余年教龄,对授课内容也比较熟悉,但是他依旧会不时检视自己的不足。他说有时候一堂课没讲好,会难过很多天。
“以前想着理论课可能会枯燥,上课中间就讲些插科打诨的学术八卦,后来担心,一个学期下来学生就只记住些旁枝末节的东西,所以就不再刻意追求热烈的课堂气氛。学术八卦嘛,一节课讲一两个就够了,总得让学生们学到些扎实的东西。”刘涛笑言,为了确保听课效果,上他的课是要交手机的。“我跟学生说,手机导致我们丧失了长时间专心致志做事情的能力。大家尝试一下两个小时不用手机,专心做一件事,哪怕不听课,自己读书也好。”
刘涛深知读书之于文学专业的重要性。上他的课,每学期精读一本书,交四次手写的读书笔记,这是硬性规定。“我专门跟学生强调,读书笔记必须手写。如果允许交打印稿,就会有敷衍的学生直接从网上粘贴复制,读书笔记也就没什么价值了。”其实这个硬性规定也给刘涛“增负”不少,一百多本读书笔记,他都得逐一翻看、打分,一个学期重复四次。
“从学生的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有些学生留言说我教会了他们读书,我很开心。其实不是我教会了他们读书,只是用这个笨办法,逼着学生去认认真真地读书。”在刘涛眼中,尽心尽责地上好每节课,认真负责地改好每本作业就是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精进之路”。
从一名华师学子成长为“桂子青年学者”,刘涛深感荣幸与压力并存。即便学术研究之路“道阻且长”,即使教书育人并非易事,刘涛相信放平心态,勤勉笃行,终将行以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