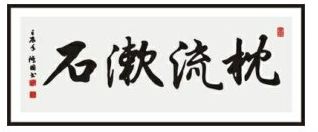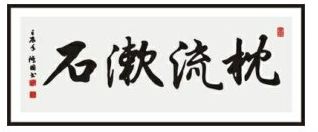
我高中时曾在学校广播站工作,起初是在周四播一些散文,后来因为太过出色了(这是站长的说法,但实际是因为缺人了)就又被调到周二播新闻。和我搭档的女生不但声音温婉好听,而且从不出错,简直是机器人。而我在她的衬托下就显得很差了,几乎几句就有一处错误。每次播完音都会攒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我心情不好时喜欢买一大推零食,然后把零食全分给舍友和班里同学,因此也算因祸得福,积攒起一点好人缘与慷慨的名声。高中毕业,不在广播站工作,心情渐好,便改掉了这个坏毛病,大学舍友们,便少了这一点福利。
去年元旦,院系文艺部有人问我要不要去做院系元旦晚会的主持人,我满口答应,并且夸口称:“我是专业的。”然而一出场便发生了个口误,当时我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将领导的名字念错,结果果然念错了。当时心凉了半截,万幸台下领导和观众们都很友好,反而给我鼓掌叫我别紧张,继续完成主持工作。这事虽然只是个晚会上的小插曲,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无法释怀,埋怨当时自己何以能发生这样的失误。
弗洛伊德有一个理论说,口误是人内心深处想法的体验。他这话或许有道理,但肯定不完全。有很多口误,完全是无心之失。比如某位央视播音员在新闻开始的时候,把“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说成了“各位好,这里是中央气象台。”这未必是因为他想要去气象台工作,而是他在从脑袋里提取词语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当然,口误的确可以反映某种信息,比如老师讲课时,讲唐诗,将清人沈德潜所编《唐诗别裁》误说成清人沈石溪所编。那我们便可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或许老师最近在读沈石溪的动物小说。
中国最早有史可稽的口误或许来自晋代的孙楚,《晋书孙楚传》中记载:楚少欲隐居,谓王济道:“吾欲漱石、枕流。”王济笑道:“流非可枕曰石非可漱。”楚道:“枕流欲洗吾耳,漱石欲厉吾齿。”这个事情《世说新语》中同样有载,孙楚是想要说他要用石头做枕头、用溪流漱口,以表现自己想要隐居的心情。无奈发生了口误,把“漱流枕石”说成了“漱石枕流”,于是王济反问道:溪流怎么能做枕头呢?石头怎么能漱口呢?孙楚反应很快,说:我用溪水做枕头是为了洗干净我的耳朵,用石头漱口是为了让磨砺自己的牙齿,巧妙地圆了过去。当然,以孙楚的口才,也不必要用石头磨牙了,他已经够能说的了。
口误是生活中极其平常的事情,人托生于肉体凡胎,没有超乎自然的能力,自然难免出现言语中的失误。即使经过专业训练的播音员,也会偶尔说错,何况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呢?所以其实不必太过在意,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偶尔的口误只是生活中一点有趣味的调剂,当时虽然尴尬,可事后旁人未必会过于苛责,也许反而觉得你真实可爱呢。倘若自认才思敏捷,也大可效仿古人,学一学孙楚,兴许还能留下一段佳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