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的高考和学校经历
——空前绝后、奇观叠出,恢复高考首届考生考试学习生活片段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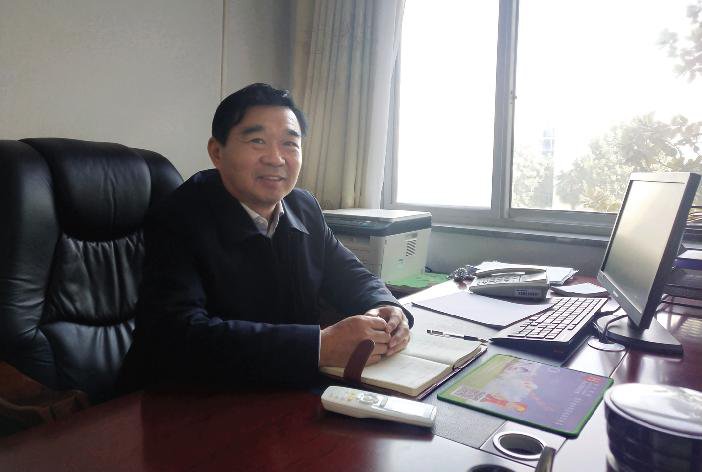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恢复高考制度后首届大学生入学40周年。
为了纪念恢复高考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我正想提笔写点什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母校商丘师范学院校友会打来的,打电话者名叫李如雪,是我的师妹,让我写篇在母校学习时的回忆文章。我说可以写,但限于水平恐怕写不好。师妹说,听说你是作家,我也喜欢文学,但却报了理科。我告诉她,我才不是什么作家呢,我也是学理科的,曾两度学习了四年物理,只不过是喜欢在工作之余写点小东西罢了。
师妹代表校友会交代了任务,那也只能是却之不恭,尊敬不如从命了。
那么写点什么呢?在这个4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幕幕镜头闪过,心绪激动难平,校园的学习生活记忆犹新,令人难忘。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从高考报名、考试、入学,直至毕业离校都是不同寻常的。
热闹的校园生活值得我们回忆的太多太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挥洒辛勤的汗水,热心传授知识;年轻有为的辅导员,循循善诱,辅导学生。教室里,同学们孜孜不倦的听讲;路灯下,同学们专心致志的读书。操场上,有同学们矫健的身影;礼堂中,有同学们嘹亮的歌声;广场上老校长向获奖者颁发奖品;大门口老教师向毕业生深情送行……这太多的镜头都值得我们努力摄取;这太多的情景都值得我们大书特书。
这一次,我还是撷取几朵高考花絮,以飨我们亲爱的校友;折几枝奇葩来奉献给师弟师妹。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恢复高考那年出现的一系列故事,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奇观。
一锤定音,大门开启。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从1966年至1976年,全国高考的大门关闭了11年,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主动分管科技教育,他以一个伟人的胆略和气魄,力主恢复高考。1977年夏季教育部在太原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仍按原来方针“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当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据说,不少老教授仍是噤若寒蝉,不敢发言,邓小平鼓励大家放下包袱,畅所欲言,但一些人只是说“我没有改造好,要好好改造”,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提议现行高招制度必须大改。而一些人仍坚持不能改,理由是原来中央定过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则建议:对当时“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可否改为“自愿报考,领导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说“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一锤定音,当场拍板,决定当年即恢复高招考试。从此开启了高招考试的大门,开启了公平公正的大门,开启了人才成长的大门,开启了青年理想的大门,开启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大门!
条件宽泛,年龄悬殊。当年参加高考的对象和条件特别宽泛,不仅仅是1966年到1976年的高中毕业生,而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包括留城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超过25周岁,未婚,都可参加考试。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还可放宽到30岁,或更高,婚否不限。事实上,当年的高考几乎是想考者则考,能考者尽考。因而考生年龄悬殊特别大,大者30多岁,小者10多岁,大小相差10到20多岁。
大潮涌动,大浪淘沙。高考制度的恢复,如沐春风,如降甘霖,如春雷惊起,如春潮涌动,如给青年们集体打了强心剂,参加高考的积极性异常高涨,全国高考如红云出岫,云蒸霞蔚,如江水出峡,万马奔腾,青年们个个摩拳擦掌,人人跃跃欲试,呈现出多届毕业生大交手,各行各业大比拼,四面八方大聚拢,五湖四海大潮涌,男女老少大鏖战的壮观景象。因此,当年参加高招人数众多,全国有考生570万人,但由于当年的大学条件所限,只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为4.79%。当年河南考生71万人,录取9374人,录取率为1.3%,录取率极低,几乎是百里挑一。当年无论考上了中专或者大学,都被群众称为“大学生“,哪村考上个大学生,就要传遍三乡五里。我们学校当年大致录取八百人,其中大专班四个班,两个数学班,两个物理班,二百人多人;中师录取十个班,后来分文科四个班,理科六个班,生化两个班,共十二个班,大致560人。
手刻试卷,草稿得分。由于当时高考时间紧,任务急,物资匮乏,缺少纸张,设备落后,因而,临时采用手工刻卷。据说,还动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制试卷。试卷纸用来印试题,答题另附纸张,考生做完题,试题纸、答题纸和草稿纸一同收缴密封,写在草稿纸上的答案,若来不及抄在答卷纸上,正确者亦可得分。
冬考春入,首届特例。因为1977年高招制度要进行改革,几经周折,最后确定恢复高考已经到了冬天,考试时间定在11月进行。记得当年我在地里“拔花柴(摘取棉花后的棉花棵,供做饭烧火用)”,拔完花柴,穿个旧棉袄就去了考场。经过改卷录取,新生入学就到了1978年的春季。这也是高考由始以来的唯一一次。
禁锢未除,“成分挡路”。1977年虽然恢复了高考制度,不论“出身成份”如何,都可以报名考试,但由于“两个凡是”左的思想的禁锢,一些高校在录取学生时仍然受到了“成份论”的严重影响,拒收了不少“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高分考生。我本人也深受其害。我清楚的记得,当年参加录取工作的物理教师马孟坤老师,在第一堂课的课间聊天时告诉我,没见你时我就认识你了,你的考分高出了本科线30多分,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别的高校不敢录取,我要了,我不怕!我感恩您———我的恩师——马老师,感恩您的胆略,感恩您的胸怀,感恩您的公平,敢恩您思想观念的超前;我感恩您———我的母校———商丘师院,感恩您的大度,感恩您的宽容,感恩您别的高校拒收后对我的接纳。
在学习期间的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这之后,我和众多的“地富反坏右”子女一样享受了平常人的待遇。
亲友扎堆,同窗共读。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考生,是中断高考12年后的第一次,考生热情高涨,踊跃报名,符合条件者几乎都想一试身手,有的师生同时报名,有的一家共同登场,有的录取到一个学校,有的录取到一个专业,因此这届同学成分复杂,职业不同,老少参差,特点各异,呈现出官民同学,师生同读,父子同校,兄弟同班,夫妻同桌的奇观。
这种奇观,在我们学校也是异彩纷呈。官民同科的如:大队支书(即现在的村支书)杨玉堂和他的村民同科就读。
师生同读的如:老师在生化班就读,其学生在文科班就读。(经征求本人意见,不愿透露姓名)
父子同校的如:其父在大专班就读,其子在中师班就读。(经征求本人意见,不愿透露姓名)
兄弟同班的如:杨思建,杨思聪兄弟;朱留峰,朱志峰兄弟。
夫妻同桌的如:王建新,杨萍夫妇;贺士海,李晖夫妇;马怀光,孔晚霞夫妇等。
对贺士海,李晖夫妇印象比较深刻,贺士海风度翩翩,有一种绅士的风度,而李晖也是雍荣华贵,有大家闺秀的范儿。
对马怀光,孔晚霞更为熟悉。孔晚霞高挑个儿,腼腆脸蛋,不爱言语,听说又是高干之女,知青下乡时就在我的邻村,体检时又是一起体检,马怀光也是那种身材魁伟,干练稳重的男士,因而至今仍有很深的印象。
“退亲”潮起,当怪不怪。因为形势政策家庭条件环境等问题的原因,一些同学特别是农村同学在大学入校前就“订了亲”,即确定了“对象”,“定了亲”的也多数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入校以后,身份环境变化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退亲”,即解除婚约,退亲现象由少而多,以至形成了一个“退亲潮”。有的是“私下消化,和平解决”,有的是双方争执不下,对方甚至找到学校,闹得不亦乐乎。我记得,在一次专题会议上,老校长关清波说:
“有的同学移情别恋,见异思迁了”。对于这些“退亲”的人,有人骂他们是当代陈世美,说与其如今,何必当初呢?有人则报以同情,认为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幸的。对此,这里不予置评,但这一现象却也折射出高考制度的恢复,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同时也可看出“十年浩劫”对人性的泯灭,对灵魂的扭曲,对情感的压抑是何等的厉害!
一篇“猜想”,万人沸腾。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1月在《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后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转载,激荡着整个科学界教育界,整个大学校园沸腾,不少同学对这篇文章爱不释手,反复阅读,细心体会。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那种默默无闻,潜心钻研,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刻苦攻关,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敢于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的精神,鞭策激励着每个学子,不少学生暗下决心,以陈景润为榜样,刻苦学习,努力拼搏,力争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整个大学校园里形成了一个比学赶超,明争暗赛的浓厚的学习氛围。我当时也算是学习比较用功的一个吧,在两次全校举行的物理竞赛中均获得一等奖第一名。
“红楼”复现,八次追看。当时正处于历史剧、古装剧、爱情剧刚刚解禁的时候。爱情剧《刘三姐》、印度电影《流浪者》,开始复映,一些同学从学校看到卫生营(附近部队的一个单位),从卫生营看到地质队,从地质队看到周边村(当时称大队),一直热情不减,兴趣不衰,越看越热。越剧《红楼梦》电影首次复映,有的同学看一遍不过瘾,就连续看了多遍。有一个“和尚班”(之所以叫“和尚班”,是因为我们这届学生男生多,女生少,其中两个班没有分到一个女生,因此同学们就给这两个班起了一个绰号叫“和尚班”)的几个同学自发组成一个团队,到距离学校十多里的商丘市道北影剧院一连看了八次。他们带着“夜光笔”当光源,明确分工,把所有唱词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刻蜡版油印成册,在同学之间传看。为了赶场子,有一次冒着大雨淋成了“落汤鸡”,但也在所不惜,照看不误。还有一次18位同学坐在公交车上,把公交车后玻璃挤碎了,司机拉到了公交车站,学校领导去交涉要人。这18位同学后来被同学们戏称为“18勇士”。
一篇“猜想”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一部“红楼”触发了同学们的情感世界。这个故事看似笑话,又像是天方夜谭。你也可能理解为这是同学们的不务正业,但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只不过是人们被压抑多年的情感的正常释放。越剧《红楼梦》电影,是部优秀影片,主题鲜明,意境高雅,不黄不色,然而因为有爱情的情节就被禁演了11年,开禁后形成了这么大的反响,这不是对“十年浩劫”文化的禁锢,精神的枷锁,情感的压抑的诠释吗?
更换“粮本”,省吃馒头。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一顿饭是白面馒头和猪肉炒粉条。要知道,这样的饭菜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每逢过年过节才可以吃到一顿两顿,而这却成了当时的家常便饭,这简直是一步登天。凭一纸“录取通知书”就换了“粮本”,当时的“粮本”每人每月供应粮食男生33斤,女生28斤,一斤食用油,香油杂油各半。还有15块5毛钱的补助金,其中主食6块6毛钱,菜金5块4毛钱,电影费五毛钱,三块钱发给个人零用。当时,馒头四分钱一个,菜两毛钱(最高价)一份,到下午可减到一毛甚至五分钱。
和现在一样,在那个年代大多数青年人都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但就个人的小目标来说,一些人追求的是“换粮本”,吃“商品粮”。
“商品粮”在当时是一个频率极高的热词。它是国家对有正式工作的国家干部和工人以及具有城镇居民(非农业)户口的粮油食品供应。有工作者每月29斤,无工作者每月27斤粮食,一斤油,粮食比例为70%白面,30%杂面。用此指标,可以购买实物,也可以按比例兑换成全国和地方流通的粮票,这是当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非农业户口”的一个待遇。这不仅仅是个待遇,也是一个极为光鲜的荣誉,很受人们羡慕。谁拥有了这个“粮本”,谁就进入了上流社会,成了贵族,成了特权阶层。别说是正式的“粮本”,哪怕是个“亦工亦农合同工”(可用自家产的粮食每月换粮票20多斤),也成了无数人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目标。因而,这也成了横在两者之间的一个鸿沟,要想逾越还真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时,得到这种待遇,除极少数靠自己的努力,绝大多数都要靠自己出生时的运气。
就因为如此,同学们都倍加珍惜。一是珍惜“粮本”来之不易,下决心努力学习,将来成才予以报尝。二是珍惜白面馒头,有的甚至舍不得吃完,节约一些拿回家让父母和家人品尝;有的则是把每月国家发放的15块5毛钱的生活费,节约一部分以接济家用。这些对后来个别常把整个馒头丢进垃圾桶的大学生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提前出圃,根植厚土。1979年临近暑假,学校召集我们1977级的学生开会,会场边上停着十几辆大轿车。会上宣布,让我们分别回到各县去实习。事实上,这消息也早有所闻,会上得到了证实。当时我们正铆足劲头,努力学习,准备大干一场,还有继续深造的“野心”,现在学了半截就被打回了原籍,大多分到农村学校去实习。当时,那种无奈、那种失落、那种痛苦的滋味儿是难以名状的。但是,那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国家想尽一切办法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让各大学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的招生。因此学校让我们尽快离校,为下一届学生腾出教室、宿舍和老师等,同时,高考和入校都恢复到秋季,也是为了便于管理。为了我们的师弟师妹,为了高校的发展,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发展,一切我们都认了。入校迟,离校早,时间短,是这届学生的一大特点,我们1978年4月8日入学,1979年9月21日离校,满打满算在校一年零五个月又13天。尽管如此,但我们还是很自豪和骄傲的,毕竟,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届我们经历了。
实践证明,恢复高考制度是非常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高考直到现在还是高校选拔学生最为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以首届为例,还是有素质的一届,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一些杰出人才,为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时代孕育大人物,大人物助推大时代,大社会产生大奇迹,大奇迹影响大社会。
生长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有邓公这样伟大的人物,他以伟大的气魄,伟大的胆略,进行了伟大地决断,力主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制度,这一决断,播种了春天的种子,播种了明天的希望,给青年插上了理想的翅膀,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我们这届学子有幸赶上这个潮头,搭上这班列车,荣幸地跨进了我们向往的母校,见证了一系列变革,目睹了一系列奇观,演绎了一系列故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而努力工作。
上述故事只是百花园中的几茹花絮,万千景致中的几个镜头。对那些镜头的回放,使人们特别是我们这些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恢复高考制度整个过程的首届考生,更有万千的感慨,丝丝的怀念,回忆中,我的思想又一次得到升华。在这里,不禁要喊出我的心里话:我敬仰您,伟大的邓公;我赞美您,敬爱的母校;我怀念您,尊敬的老师;我想念您,亲爱的同学;我热爱您,可爱的校友!
(作者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侯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