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道,见人心
——《陌上》印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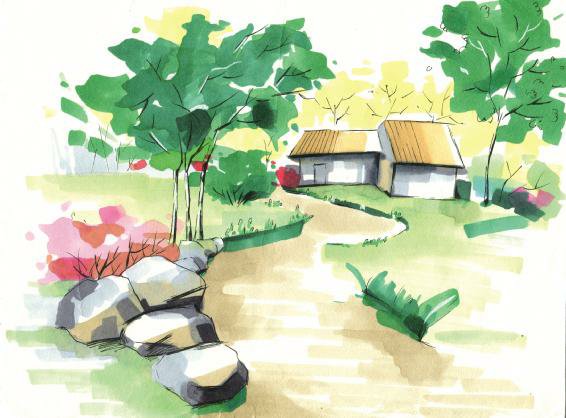
李梦迪 绘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看作一个本质上的乡土社会是颇有见地的。传统性实质上就是乡土性,它与以城市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文明具有天然的对立和矛盾。在《陌上》印象(一)中,我梳理了付秀莹灵动飞扬充满欢腾的日常语言,带领读者从语言层面进入当下现代乡土中国的缩影——芳村。不错,“它干净、整洁、素雅,带着乡野的清风”,然而,在风轻云淡的“细细叙述”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作者付秀莹的“凶狠的诚实”,这个凶狠,表现在她对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乡村的复杂现实深刻和清醒的认识,是采取直面而不是侧面的姿态,更不是用诗意或者美学的滤光镜把客观现实中的矛盾和残酷滤掉。
小说设置了楔子和正文两部分,分别讲述芳村的过往和当下,前者是作者记忆中的芳村,也是芳村的理想模样,那时的芳村,向往物质却并不贪婪,讲究节气敬畏传统,有着相对整齐而明晰的秩序感。然而,那只是《陌上》的遥远的背景,当下的芳村,失去了往日的芬芳,风沙满面,惶恐不安。
正文里的芳村,是破败、颓废、崩塌的价值乱象,虚无、拜金、欲望、焦虑处处滋长。在当下的芳村,有着绝对震慑力和话语权的,不再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者,而是那些在经济上拥有优势的人。无论这些人在道德上有着怎样的瑕疵甚至缺陷,无论他们的经济优势通过何种方式获致,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芳村呼风唤雨的位置和能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完全受物质力量的支配和控制。即使是身居芳村政治结构中最高层的村委会主任建信,在当地首富大全耀眼金钱光晕的威逼之下,也不得不甘拜下风,甚至在关键时刻还要仰仗大全出手相助。芳村的头号人物,不是建信,而是大全。
家庭内部的人伦关系也在发生着触目惊心的变化。传统的婆媳往往是严厉苛责的婆婆和逆来顺受的儿媳,然而在《陌上》里,传统的婆媳关系早已经颠倒,猫和老鼠交换了角色。翠台和儿媳爱梨,喜针和儿媳梅,兰月她娘和儿媳敏子,她们之间那些明争暗斗,微妙的较量,隐秘的敌意,甚至儿媳对婆婆的公然辱骂,婆婆给儿媳当众下跪,种种境况,都令人心惊。家庭中“父亲”的权威早已不在,随着“父亲”的年老体衰以及劳动能力的丧失,父亲在家庭伦理中渐渐变为为弱势,需要仰子女鼻息度过晚年。《陌上》里,老莲婶子在老伴病重时,为了不看儿女脸色,不使儿女为难和嫌弃,决然拔掉了老伴赖以续命的输液针管。而她自己,在老病相逼的时候,不堪儿女的漠视和厌弃,喝农药走了绝路。兄弟之间,姊妹之间,夫妇之间,他们的关系、情感以及相处方式,都有可能在物质的强大作用之下,发生扭曲和变异。这种关系的颠覆和重构,是当下中国乡土文化新的变化。
《陌上》还讲了在现代工业的大量入侵下,人与土地关系的日渐松散和冷漠,《陌上》无数次描写繁茂的庄稼地,庄稼们在一年四季里的种种风致,以及人们精心操办的各种节气和婚丧嫁娶的隆重仪式,其实包含了哀婉、眷恋的不舍的深情,有挽歌的意思在。微风吹来泥土的气息和那些高高矗立的工厂里轰鸣的机器,二者彼此呼应,令每一个熟悉并热爱乡村生活的人,顿生今昔之叹。
《陌上》的芳村,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扭曲和异变的乡土,是费孝通对传统乡土的哀婉的挽歌。它寄托的,不仅仅是付秀莹的乡愁,更是一个时代的新乡愁,是中国的新乡愁。在万般滋味中,见天地,见世道人心。
